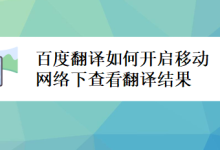川劇不像黃土高原的秦腔那樣蒼涼悲愴,也不像魚米之鄉的昆曲那樣多情繾綣,飄蕩在巴山蜀水之間的川劇,有著四川人獨特的既熱辣豪朗又閑適幽默的性情。
蜀地自古就是歌舞戲劇之鄉,早在唐代就有“蜀戲冠天下”的說法。隨著清代的大移民,四川本地戲融合吸收了外來戲種,融匯了高腔、胡琴、昆腔、燈戲、彈戲五種聲腔,人稱“五聲共和”。
川劇不僅聲腔豐富屬全國少有,而劇目更是多如繁星,素有“唐三千,宋八百,數不完的三列國”之說。《拉郎配》、《喬老爺上轎》等經典喜劇,把四川人特有的機智幽默,表現得活靈活現妙趣橫生。

不過,使川劇名揚天下并走向世界的,卻是川劇的絕活。一說起川劇絕活,人們立刻會聯想到變臉,聯想到香港天王劉德華拜師學變臉的故事。
變臉在戲劇中能夸張地表現人物的情緒起伏,烘托出“相隨心變”的藝術效果。變臉的手法很多,主要有運氣變臉、吹臉、抹臉、扯臉。
運氣變臉現在已經無人能做到,傳說已故川劇名演員彭泗洪扮演《空城計》中的諸葛亮,當琴童報告司馬懿大兵退去后,他能夠運氣而使臉由紅變白,再由白轉青,表現諸葛亮如釋重負的復雜心情。
吹臉是用巧力把金粉、銀粉、墨粉等吹在臉上,瞬間變色。有的做法是在舞臺的地面上擺一個很小的盒子,內裝粉末,演員到時做一個伏地的舞蹈動作,趁機將臉貼近盒子一吹,粉末撲在臉上。
但必須注意的是:吹時閉眼、閉口、閉氣。《活捉子都》中的子都,《治中山》中的樂羊子等人物的變臉,采用的便是“吹臉”的方式。
抹臉通過抹油彩的手法,將化妝油彩涂在臉的某一特定部位上,到時用手往臉上一抹,便可變成另外一種臉色。如果要全部變,則油彩涂于額上或眉毛上。如果只變下半部臉,則油彩可涂在臉或鼻子上。
目前的川劇變臉多數采用的是扯線變臉技法。扯臉技法經歷了從揭硬紙殼臉譜、揭草紙臉譜,到扯絲綢臉譜的發展演變,康止林、孫德才、劉忠義、王道正、彭登懷等一代代川劇藝術家都為之做出了貢獻。
絲綢扯線法是事先前將臉譜畫在一張一張的綢子上,每張臉譜上都系上絲線,再一張一張地貼在臉上。 絲線則系在衣服的某一個順手而又不引人注目的地方 -如腰帶上之類。
隨著劇情的進展,在舞蹈動作的掩護下,一張一張地將它扯下來。這考的是手快功夫,一般的學生學上一年半載年也能變出3、4張臉來,但要變出更多張臉譜,就需要長久的苦功了。
1985年,王道正在香港飾演《白蛇傳》中的缽童,變出綠、紅、白、黑等八張不同的臉,名震港島。后來,《白蛇傳》赴東京公演,在六部攝像機的錄相監測之下,日本人依然無法探知變臉的奧妙。
此后,王道正多次應邀專門表演變臉,才使變臉成為獨立表演的節目,也迎來了變臉的光輝歲月。1999年,彭登懷用25秒變了14張臉。他在電視劇《笑傲江湖》中引入變臉神技,讓金庸先生連連稱絕,稱贊不已。

不過,除了變臉,川劇絕活有很多:藏刀、變髯口-胡須、踢慧眼、耍獠牙、吐火、滾燈等等都非常精彩。
這些川劇絕活往往不是孤立生硬地存在于戲中,而是跟劇情發展、人物性格結合在一起,作為刻畫人物推動劇情的一種或夸張或浪漫的手法。
著名的川劇《皮金滾燈》,講的是皮金的老婆頗有川妹子的潑辣勁兒,因為皮金賭博成癮屢教不改,為了教訓這個浪子。
老婆等皮金輸光回家,端了一盞油燈來讓他頂在光頭上,要他頂著燈聽口令左扭右擺、鉆板凳、翻跟斗,做出各種高難度翻滾動作,在驚險與幽默中反映了夫妻間又愛又恨的情趣,充分演繹了成都人的“耙耳朵”故事。
還有踢慧眼,民國時期的“戲圣”康止林扮演《水漫金山寺》中的韋陀,隨著他唱一聲“待吾睜開慧眼一觀!”然后,將一只事先貼在靴尖上的慧眼,踢至雙眉之間粘上,立刻變出第三只眼來。

到成都的游客,一般去寬窄巷子、錦里、琴臺路的茶樓看變臉,也可以在皇城老媽和大妙火鍋一邊燙著火鍋一邊看變臉。
不過,最地道的川劇,還得去那些老茶鋪里,比如百年老店悅來茶館,一把竹椅子,一碗蓋碗茶,優哉游哉地品茶、聽戲,在抑揚頓挫的蜀聲古韻中享受成都的市井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