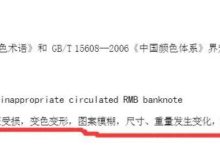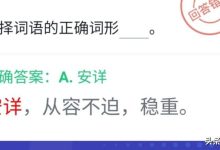要理性面對老人去世比往年多很多“新十條”出臺馬上就“滿月”了從最初人們的“期盼”熱情,到具體的“不得”、“不按”、“不要”、“不查”、“不再”等措施的落實,之后又經歷了囤藥、搶藥、感染波峰、就醫波峰、火化波峰,到現在“脆弱人群”及“脆弱人群的家屬”依然處于焦灼之中。
粗略估計,超一線城市和一線城市正在經歷感染波峰、就醫波峰、火化波峰,次一級城市或再次一級城市,依次類推人口量級從大到小,從城市到鄉鎮再到農村將逐步經歷感染波峰、就醫波峰、火化波峰雖然理論上是這樣的情況,但是關于“老人去世比往年多很多”卻早已成為“放開”后人們最直接的印象,并且這個印象很難從人口量級層面簡單地進行區分。
不過針對這個問題,有專家順著記者的提問,進行了相應的回應記者:“大家從自己的親朋好友之間總是能聽到自己家里老人有去世的這種情況,好像比往年要多很多?”專家:“肯定會多,這一點我們要承認但是大家想一想,你身邊的人陽了多少?或者一家人可能都陽了,有幾個危重的?或者有幾個肺炎的?這個大家應該心里有數吧。
”緊接著記者反問:“感覺是這樣?”專家:“有吧,因為現在沒法統計具體的數,為什么?我們不知道分母,因為現在不再做全員核酸,也不再做抗原甚至說很多人在家里就待幾天,有癥狀也好,無癥狀也好,在家里扛一扛就過來了,就上班去了。
所以說可能我們大家都陽過了,但是我們并不知道這個分母是多少”直觀來看,這兩段“專家答記者問”確實沒多少信息量,更像是對當前疫情形勢的一種簡要概括可這卻是“放開”后,比較正面的一次回應“死亡多”的問題,雖然給出的答案依然比較模糊,用的是“肯定會多”,但是也比較厚實的強調“這一點我們要承認”。
并且就具體的釋疑來看,專家更傾向于解釋現象,而非是解釋原因對此輿論層面當然是“不淡定”的,比較廣泛的反應是專家們就會“輕飄飄”從某種意義上講,輿論層面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定性,并不在于專家們說了什么,而是從“新十條”以來,部分人依然在根據結果爭議“放開”對,還是“不放開”對,也就是對于防疫始終還是停留在兩級立場上。
可事實上,防疫從來就不是簡單的對或錯的問題,也不是簡單的有標準答案的問題而是錯綜復雜、難以預料的問題就比如關于“藥緊缺的問題”,專家的解釋是,有市場供需的問題、有恐慌導致的囤藥、搶藥的問題、也有老齡化的問題,還有就是對優質醫療資源的集中需求的問題。
也就是說,很難用簡單地“為何不提前配置的思維”去進行無縫銜接并解決問題而且“新十條”的出臺,它本身面對的是“生命安全”、“生活便利”、“經濟活力”等等之間的綜合抉擇如此之下,意味著復雜之下還有更復雜,所以是很難一概而論的去定性和解決的。
由此再去面對專家釋疑,只能說在沒有數據支撐的現實下,他(她)們也只能把話講到那個程度否則單純地為迎合部分人想聽“老人去世比往年多很多”,才是真正的不負責任或不專業平心而論,任何人因為感染新冠離世都是值得悲傷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都是“放開”的原罪。
甚至不夸張地講,總把“放開”的原罪掛在嘴邊,才是一種偏狹和短視要明白一點,在面對疫情的問題上,從始至終就不存在萬全之策,也就是說不管是“放開”,還是“不放開”都將承受必然的損失,而且在這個問題上,疫情已經三年,就是再沒有受到沖擊或影響的人群,應該也有基本的認識了。
所以這種時候,動輒還在拿“板子沒打到自己身上就會輕飄飄”進行陰陽怪氣,只能說這些人壓根兒就沒搞明白疫情到底意味著什么事實上,“新十條”出臺前后,有專家就提到這不是“全劇終”,而是“新挑戰”,可當時有些支持“放開”的人卻強調專家想“往回走”。
提調這個問題就想說,無論是支持“放開”,還是支持“不放開”,都最好不要陷入非黑即白的境地否則所謂的“既要”、“又要”、“還要”根本就沒有可周旋的余地因為我們很清楚“既要”、“又要”、“還要”要想有周旋的余地,起碼的前提是,不能把可能的損失都歸結為疫情防控調整,要不然疫情防控還怎么調整。
之所以這樣講,并不是認為異見不能提,而是異見的提出一定是基于現實而言的就如“專家答記者問”中提到的“你身邊的人陽了多少?或者一家人可能都陽了,有幾個危重的?或者有幾個肺炎的?這個大家應該心里有數吧”,其實并不是為否認“老人去世比往年多很多”這個事實,而是想說就算“多很多”,對于多數人來講,它仍然是個邊緣事實。
也就是說“很多人在家里就待幾天,有癥狀也好,無癥狀也好,在家里扛一扛就過來了,就上班去了所以說可能我們大家都陽過了,但是我們并不知道這個分母是多少”的這個說法,更符合多數人的感受,而非是人人都好像面臨著“火化波峰”。
另外,其實對“就醫波峰”和“火化波峰”有了解的人來講,每年冬天都會迎來好幾波“就醫波峰”和“火化波峰”提調這個事實是想說,即便新冠疫情加重了“就醫波峰”和“火化波峰”,但也要清楚,不能把最近離世的人都歸結為“新冠死”。
換句話說,不管是面對“老人去世比往年多很多”,還是面對專家們的釋疑,都不要上來就往“敵意”上理解說實話,面對具體人的離世,就算非親非故,也沒有人會認為那個人就該離世而之所以會出現看起來“輕飄飄”的說法,就在于面對不確定性的疫情,我們總需要用確定性的態度去應對,否則只會被疫情拖得更加無法應對。
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用戶上傳并發布,未作人工編輯處理,不構成投資建議請自行甄別,也不承擔相關法律責任。如果您發現有涉嫌版權的內容,歡迎發送郵件至:wolfba@qq.com 進行舉報,并提供相關證據,工作人員會在5個工作日內聯系你,一經查實,本站將立刻刪除涉嫌侵權內容!
大智網匯
版權聲明:本文內容由互聯網用戶自發貢獻,該文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僅提供信息存儲空間服務,不擁有所有權,不承擔相關法律責任。如發現本站有涉嫌抄襲侵權/違法違規的內容, 請發送郵件至 wolfba@q.com 舉報,一經查實,本站將立刻刪除。
投稿&軟文
覺得文章有用就打賞一下文章作者
非常感謝你的打賞,我們將繼續提供更多優質內容,讓我們一起創建更加美好的網絡世界!
微信掃一掃打賞

 哺乳期飲食指南:能否享受美味的豆腐?-哺乳期媽媽能否安心食用豆腐?營養專家為您解答
哺乳期飲食指南:能否享受美味的豆腐?-哺乳期媽媽能否安心食用豆腐?營養專家為您解答 高鐵上大學生幫了11歲時的自己-5月6日上午熱點新聞
高鐵上大學生幫了11歲時的自己-5月6日上午熱點新聞 張志磊比帕克重40斤-張志磊大戰帕克誰能贏?中國專家:帕克比喬伊斯更難打
張志磊比帕克重40斤-張志磊大戰帕克誰能贏?中國專家:帕克比喬伊斯更難打 專家:朝鮮半島炮聲轟隆局勢很嚴峻-朝突然動手,黃海方向傳出炮聲,韓美怕了?美軍為撤退鋪路!
專家:朝鮮半島炮聲轟隆局勢很嚴峻-朝突然動手,黃海方向傳出炮聲,韓美怕了?美軍為撤退鋪路! 網傳「不宜流通人民幣紙幣新規意在推數幣」,專家回應「系誤解,現金將長期存在」,哪些信息值得關注?
網傳「不宜流通人民幣紙幣新規意在推數幣」,專家回應「系誤解,現金將長期存在」,哪些信息值得關注? 男子 29 年無償獻血 381 次被疑夸張,專家稱「理論最高可獻 696 次」,獻血有次數限制嗎?
男子 29 年無償獻血 381 次被疑夸張,專家稱「理論最高可獻 696 次」,獻血有次數限制嗎? 李躍華稱「用好苯酚再無疫情」引專家質疑,其診所每天數十人排隊求醫,哪些信息值得關注?
李躍華稱「用好苯酚再無疫情」引專家質疑,其診所每天數十人排隊求醫,哪些信息值得關注? 專家回應建議拿出三分之一存款買房-手中有50萬現金,選擇“買房”還是存
專家回應建議拿出三分之一存款買房-手中有50萬現金,選擇“買房”還是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