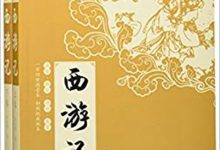大河報(bào)記者在地下700米體驗(yàn)煤礦工熱心跳
煤礦小巷連接著兩個(gè)世界:一個(gè)井,充滿色彩;一個(gè)地下,黑暗和潮濕。煤礦工人的生活軌跡更像是一條狹窄的通道,連接著兩種生活:一個(gè)地面,一個(gè)地面;一個(gè)明亮,一個(gè)黑暗。
每個(gè)礦工背后都有一個(gè)鮮為人知的故事,里面有淚水、歡笑、喜悅和悲傷。他們每天深入漆黑的地下,連續(xù)幾個(gè)小時(shí)進(jìn)行高強(qiáng)度的作業(yè);他們犧牲了享受光明的權(quán)利,卻為成千上萬的家庭點(diǎn)燃了夜晚的燈光。
大河日?qǐng)?bào)大河客戶記者呂高見習(xí)記者李帥文記者趙龍飛攝影
核心提示!黑塵堆積在身上,刻在臉上,挖出滾燙的熱情,灑滿了人間的光芒…一首《礦工之歌》唱出了無數(shù)煤礦工人的艱辛和心聲。
“礦燈、安全帽、防水鞋、自救器……”這是煤礦工人下井的必備品。進(jìn)入直線距離700多米深的地下,需要穿過10多里狹長潮濕的曲線巷道,在地下工作8小時(shí)。在到達(dá)目的地之前,需要乘坐多輛纜車。
一線煤礦經(jīng)常覆蓋著厚厚的煤灰;挖掘現(xiàn)場,打破一點(diǎn)堅(jiān)硬的巖層,平均每天推進(jìn)9米。盡管數(shù)百米的地下工作非常困難,但他們?nèi)匀粺釔圻@個(gè)職業(yè)。8月底,《大河日?qǐng)?bào)》記者分為兩種方式,記錄不同工種煤礦工人的真實(shí)工作和生活。
安檢準(zhǔn)備
換工作服,甚至換內(nèi)衣
8月30日,平頂山,中雨。
凌晨4點(diǎn),北方的天空逐漸變白,遠(yuǎn)處的一座礦山冒著煙。當(dāng)城市里很多人還在睡覺的時(shí)候,礦工們的工作和生活早就開始了。
平煤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二礦,偶爾有一列運(yùn)煤火車經(jīng)過大門。礦工們來來往往匆匆忙忙。有的剛下班升井,有的趕著上班,在雨中穿梭。《大河日?qǐng)?bào)》記者一路跟隨綜采一隊(duì)采訪,主要負(fù)責(zé)地下采煤。據(jù)了解,早期礦工只檢查機(jī)械設(shè)備和地下安全。為了更真實(shí)地記錄他們,記者不得不跟隨下一個(gè)團(tuán)隊(duì)。
上午10點(diǎn),綜采隊(duì)。在一層一層的房間里,近20名礦工聚集在這里,上班前正在召開安全例會(huì)。據(jù)團(tuán)隊(duì)書記張建文介紹,他們每天下井前都會(huì)舉行這樣的例會(huì)。
隨后,礦工們來到員工餐廳吃飯,里面有各種各樣的烹飪和主食。記者注意到,大多數(shù)礦工喜歡吃燉面條,一大盆燉面條只需8元,既實(shí)惠又方便。
晚飯后,礦工們開始換衣服,穿著藍(lán)色工作服,礦燈、安全帽、防水鞋、自救器等。記者和礦工一樣,包括內(nèi)衣在內(nèi)的衣服也應(yīng)該換成棉質(zhì)工作服,甚至手表和項(xiàng)鏈也不允許穿。不僅因?yàn)榈叵屡K,還因?yàn)榉乐箓€(gè)人衣物摩擦產(chǎn)生靜電,火花引起瓦斯爆炸。礦工全副武裝后,他們聚集在一起,各自打卡后,接受入井前的安全檢查。
“全身都要摸,除了規(guī)定的物品,其他物品都不允許攜帶。”據(jù)現(xiàn)場檢查的一位師傅說,頭頂有攝像頭監(jiān)控,直接連接到集團(tuán),礦工在工作中很有意識(shí)。
下井作業(yè)
坐纜車往返需要3個(gè)小時(shí)。
井口是一排排架空成人纜車來回循環(huán)。礦工們通常被稱為“猴車”。人們像猴子一樣坐在上面。
纜車離地大約半米遠(yuǎn)。記者坐在其中一輛纜車上。一開始,他搖晃得很厲害,雙手緊緊地握著,擔(dān)心自己會(huì)從上面摔下來。沿著陡峭的小巷向前行駛。雖然速度不是很快,每隔20或30米就有熒光燈,但小巷仍然昏暗潮濕。偶爾,你可以看到老鼠經(jīng)過。
記者注意到,許多礦工下班回來時(shí)都覆蓋著煤灰,工作服上的反射條特別引人注目。一些礦工手里拿著一本書,利用安全帽上的礦燈來打發(fā)無聊的時(shí)間。
記者在采訪中發(fā)現(xiàn),每次乘坐纜車大約需要半個(gè)小時(shí),到達(dá)車站都會(huì)有語音提醒,以防止礦工通過車站。每隔一段距離就會(huì)有一個(gè)垃圾箱,一些礦工拿著掃帚和編織袋坐在纜車上清潔。
坐纜車后,再走幾公里。經(jīng)過幾扇封閉的門后,里面的溫度瞬間升高。過了一會(huì)兒,記者汗流浹背,工作服緊緊地貼在身上。沿途懸掛著許多引人注目的安全標(biāo)語,巷道兩側(cè)有許多瓦斯檢查記錄牌,上面清楚地記錄著溫度、瓦斯等數(shù)據(jù)。在任何地方,陪同記者采訪的技術(shù)人員王勇勇都會(huì)上前仔細(xì)檢查。此外,巷道內(nèi)的墻壁上還有許多瓦斯孔,據(jù)礦工介紹,這些孔一般深約100米,“安全始終放在第一位”。
“路上要轉(zhuǎn)五輛纜車,中間要走路,往返三個(gè)小時(shí)才能到達(dá)。”據(jù)礦工介紹,除了工作幾個(gè)小時(shí),他們每天在路上下井的時(shí)間更多。
巷道掘進(jìn)
使用先進(jìn)設(shè)備,平均每天向前推進(jìn)9米

中午12點(diǎn)10分,《大河日?qǐng)?bào)》的另一名記者跟隨掘進(jìn)隊(duì)的礦工到達(dá)了700多米深的地下掘進(jìn)面。這是一條正在挖掘的小巷,從上個(gè)月10日起,他們開始了小巷。
剛走進(jìn)掘進(jìn)巷道,記者就覺得這條巷道比沿途的巷道特別寬敞。頂部高3.1米,寬4.85米。為了防止頂部巖石脫落,整條巷道由u形鋼支架支撐,上面有一層由粗鋼絲制成的鋼網(wǎng)。巷道中間有一條寬約兩米的運(yùn)輸帶,可以將破碎的石塊和煤塊運(yùn)輸?shù)降孛嫔稀?/p>
巷道掘進(jìn)的前端是一臺(tái)58噸重的掘進(jìn)機(jī),前面是一個(gè)巨大的炮頭,上面覆蓋著合金制成的截齒,用來挖掘夾雜著煤層的巖壁。炮頭下面是一個(gè)厚重的鏟板,兩側(cè)有一個(gè)巨大的金屬輪,可以將破碎的巖石和煤轉(zhuǎn)移到掘進(jìn)機(jī)下面的運(yùn)輸帶上。一名礦工在現(xiàn)場告訴記者,這臺(tái)挖掘機(jī)平均每天可以向前挖8米到9米,這是一種先進(jìn)的設(shè)備。
下午1點(diǎn),做好各項(xiàng)安全檢查后,開始挖掘。隨著挖掘機(jī)的啟動(dòng),巷道前方突然彌漫著煤塵。
一名礦工坐在掘進(jìn)機(jī)的最高部分。他是一名觀山工,負(fù)責(zé)指揮掘進(jìn)機(jī)的掘進(jìn)方向。根據(jù)觀山工的指揮,旁邊駕駛座上的司機(jī)掏空巖壁上部的巖石后,負(fù)責(zé)組裝鋼支架的礦工將立即抬起組裝好的u型鋼支架,并將其運(yùn)送到剛剛掏空的巖壁上,并將其支撐在掏空的巖壁上。隨后,掘進(jìn)機(jī)會(huì)慢慢掏空巖壁下部,組裝人員也會(huì)隨著進(jìn)度固定剛支撐的u形支架。就這樣,掘進(jìn)約50厘米,固定了u形支架,隧道越來越深。
記者跟隨礦工運(yùn)輸材料,試圖幫助運(yùn)輸未組裝的鋼支架,但剛剛舉起,沉重的鋼壓在手臂上突然失去了力量。據(jù)一名運(yùn)輸?shù)V工說,這些鋼,一個(gè)重量超過170金,四個(gè)可以組成一個(gè)完整的鋼支架。
采煤現(xiàn)場
地下溫度較高,礦工仍堅(jiān)守崗位
一個(gè)半小時(shí)后,中午12點(diǎn)多,《大河日?qǐng)?bào)》記者跟隨采煤礦工,走過狹窄的小巷和鋪在地上的軌道,到達(dá)了收集面一線作業(yè)現(xiàn)場附近。在我走近之前,我聽到了一聲刺耳的機(jī)器轟鳴聲。
越往里走,越難走。其實(shí)不叫路。有些地方只能讓一個(gè)人側(cè)身通過,更難走的地方要彎腰低頭才能慢慢通過。有時(shí)候如果不注意,頭頂上的頭盔會(huì)碰到巷子上方的巖石,發(fā)出“叮當(dāng)”的聲音。
在最深的一線采煤現(xiàn)場,許多礦工正在工作。他們是以前的團(tuán)隊(duì),還沒有下班。該團(tuán)隊(duì)指揮采煤機(jī)礦工王俊波手持遙控器,指揮機(jī)器運(yùn)行。不到5分鐘,巷道墻上就挖出了一個(gè)長方形的洞,煤塊不斷滾落,直接進(jìn)入運(yùn)輸機(jī)。
“控制采煤機(jī)最重要的是讓它聽話。除了掌握高度外,記住不要切割煤頂部或底部的巖石。王俊波指著作業(yè)區(qū)的煤堆說,切割高,不安全;如果切割低,巖石與煤混合,煤炭質(zhì)量差,影響后續(xù)銷售價(jià)格。他介紹說,采煤機(jī)在巷道里不停地來回移動(dòng),一刀下來就能拿到60厘米寬的煤塊。采煤機(jī)上有水管,不停地往采煤機(jī)滾筒上灑水降塵。
據(jù)了解,挖掘后可以采煤,采煤前應(yīng)安裝運(yùn)輸機(jī)和支架。20多人三班倒,有時(shí)大約需要半個(gè)月的時(shí)間來改進(jìn)電力、運(yùn)輸系統(tǒng)、管道等。只有在所有的氣體和其他設(shè)備都達(dá)到標(biāo)準(zhǔn)后,才能采煤。
班長李順生透露,地下是男人的天堂。因?yàn)橄旅娴臏囟忍撸芏嗳讼矚g赤手空拳工作。如果有無盡的工作,礦友會(huì)上前幫忙,整天和鐵家伙打交道,小碰撞時(shí)有發(fā)生。“但安全必須放在第一位。”他說。
人物講述
三代礦山玩58噸掘進(jìn)機(jī)
下午1點(diǎn),在掘進(jìn)面的巷道里,記者看到郭石磊剛從掘進(jìn)機(jī)下鉆出來,負(fù)責(zé)掘進(jìn)機(jī)的維修。他不僅是一個(gè)能玩58噸掘進(jìn)機(jī)的90后,也是一個(gè)地地道道的礦三代。這時(shí),他剛剛修復(fù)了掘進(jìn)機(jī)底部滾動(dòng)托輪上的一個(gè)小問題,汗水和煤灰完全掩蓋了他24歲的真實(shí)年齡。因?yàn)樗€有工作要做,所以面試必須等到他完成工作回到地面。
隨后,在地上的一間辦公室里,剛洗完澡,一身白凈的郭石磊出現(xiàn)在記者面前。他出生于1993年,家鄉(xiāng)在商丘。2011年3月,他來礦上工作,剛開始只是一名普通的掘進(jìn)工,每天都像其他掘進(jìn)工一樣,做著運(yùn)輸、掘進(jìn)的工作。2015年下半年,單位培養(yǎng)年輕人才時(shí),他入選,現(xiàn)成為掘進(jìn)機(jī)維修人員。“我爺爺是二礦的礦工,也是礦上的第一批礦工。現(xiàn)在我和爸爸、叔叔、叔叔都在二礦工作,我可以說是一個(gè)地地道道的礦三代。郭石磊自豪地說。
“我現(xiàn)在的日常工作是對(duì)掘進(jìn)機(jī)進(jìn)行維修,我已經(jīng)掌握了很多關(guān)于掘進(jìn)機(jī)的維修技巧。“說到工作,郭石磊高高興興地說,雖然掘進(jìn)機(jī)是一個(gè)“愚蠢的大”,但真的想打開,只要有人幫忙或很容易組裝,畢竟,整個(gè)掘進(jìn)機(jī)重58噸,一條拆卸的履帶有78噸。現(xiàn)在他每天比生產(chǎn)工人早起,早上5點(diǎn)多點(diǎn)名,然后吃飯,換衣服下井維護(hù)挖掘機(jī),有時(shí)時(shí)時(shí)時(shí)間緊,他會(huì)直接帶早餐下井。如今,在維修掘進(jìn)機(jī)時(shí),爬、躺、鉆已成為他的家常便飯,他可以通過聽掘進(jìn)機(jī)運(yùn)行的聲音來判斷其存在的小問題。
談到近年來的工作經(jīng)驗(yàn),郭石磊尷尬地說,當(dāng)他第一次工作時(shí),他覺得礦工是一個(gè)底層工人,沒有臉,不好意思告訴同學(xué)和朋友他是礦工。直到后來,當(dāng)他真正了解了現(xiàn)代礦工的工作環(huán)境時(shí),他才覺得他以前的想法很荒謬。”我認(rèn)為成為一名礦工很好,但我有點(diǎn)累了。”
技術(shù)更新
現(xiàn)在有了掘進(jìn)機(jī),不僅效率高,而且節(jié)省了礦工的體力
46歲的吳東宇是一名支架工,也是礦山采煤明星。他在一線采煤工作了20多年,經(jīng)歷了三次改革。談到變化,他高興地告訴記者:“現(xiàn)在更安全了,工作也更容易了。”。
“獻(xiàn)出你的一生,獻(xiàn)出你的兒子。”他半開玩笑地說,他的兒子在另一個(gè)團(tuán)隊(duì)工作。雖然他們都在地下工作,但他們很少見面。有時(shí)他們?cè)诶|車上相遇,雙方只能打招呼,大喊大叫。
在接受地下掘進(jìn)采訪時(shí),記者還見到了在掘進(jìn)隊(duì)工作了26年的彭隊(duì)長。彭隊(duì)長告訴記者,在他26年的礦工生涯中,他見證了掘進(jìn)工作的逐步改進(jìn)。“從最早的射擊、手動(dòng)裝載,到后來用耙斗機(jī)裝載,到今天的掘進(jìn)機(jī),掘進(jìn)工作確實(shí)比以前好多了。”
彭隊(duì)長說:“當(dāng)我們第一次使用火藥時(shí),我們不僅要做大量的安全工作,防止瓦斯爆炸,而且工作效率也不高。我們每天最多可以挖兩三米。”。現(xiàn)在有了掘進(jìn)機(jī),就完全不同了。掘進(jìn)機(jī)可以挖掘巖層,并通過皮帶直接將破碎的巖石和煤塊運(yùn)輸?shù)降孛妗F骄刻炜上蚯巴诰?米至9米,不僅效率高,而且節(jié)省了大量體力。
為了安全起見,在下井前,礦方一再告訴記者禁止攜帶任何電子設(shè)備。因此,面對(duì)地下礦工生活的艱辛和許多感人的畫面,記者未能通過鏡頭逐一記錄下來。然而,礦工的安全是每個(gè)人努力工作的目標(biā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