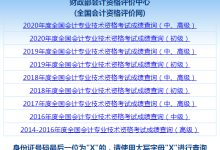不僅如此,媒體報道顯示,被虐待兒童的親屬在探親時“注意到小浩身上的傷疤”。那么,與受害者共同生活的其他家庭成員、鄰居和基層組織是否對兒童的虐待負責呢?為什么家人和鄰居偶爾看到別人能看到的傷疤都視而不見?為什么同樣是監護人的母親對此不置一詞,她是否也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監護人的施虐過程是否伴隨著被害人的呼救,為什么周圍能及時干預的力量在類似情況下處于失敗和失語狀態?
“我兒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別人管不了。”用現代人倫觀念、基本法理甚至明文法律法規駁斥這種無知的觀點可能并不難,但難的是改變縱容和忽視這種謬誤的社會環境。打孩子打女人是“家務”,別人不方便干預,更別說報警了。頑固的社會氛圍讓人無奈。
應該承認,持有類似觀點的父母并不少,但可能沒有這種情況那么嚴重。社會土壤的改善可能需要很長時間,可能真的需要重復虐待案件來喚醒更多的人從厭惡、蔑視到干預家庭虐待行為,然后及時果斷地報警尋求幫助。
嬰兒從出生起就是一個受法律保護的獨立個體。相關法律對未成年人的保護和家庭暴力的反對始于預防違法犯罪,明確有責任及時發現和提供包括醫院、學校和基層社區在內的線索。2020年5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會同教育部、公安部等9個部門,共同建立了侵犯未成年人案件的強制報告制度。在實踐層面,可以看出“及時報告”的案件,但對忽視報告的追溯和處罰仍然很少。
早一點,早一點,每次孩子被虐待,外界都希望盡快介入救援。要讓旨在“救孩子”的制度硬起來,扎實起來,事后不要總是被困在后悔中。求助救助兒童,深入研究茂名男孩虐待案的每一個細節,發現案件發現前每個可能干預節點的每一個環節的疏漏,是社會在幫助被虐待男孩籌集資金,呼吁嚴厲懲罰“不值得父母”的嫌疑人之外所能做的微薄工作。
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用戶上傳并發布,未作人工編輯處理,不構成投資建議請自行甄別,也不承擔相關法律責任。如果您發現有涉嫌版權的內容,歡迎發送郵件至:wolfba@qq.com 進行舉報,并提供相關證據,工作人員會在5個工作日內聯系你,一經查實,本站將立刻刪除涉嫌侵權內容!
大智網匯
版權聲明:本文內容由互聯網用戶自發貢獻,該文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僅提供信息存儲空間服務,不擁有所有權,不承擔相關法律責任。如發現本站有涉嫌抄襲侵權/違法違規的內容, 請發送郵件至 wolfba@q.com 舉報,一經查實,本站將立刻刪除。
投稿&軟文
覺得文章有用就打賞一下文章作者
非常感謝你的打賞,我們將繼續提供更多優質內容,讓我們一起創建更加美好的網絡世界!
微信掃一掃打賞

 大金空調除濕功能詳解:標志含義與使用指南-大金空調除濕標志:了解含義,掌握使用技巧
大金空調除濕功能詳解:標志含義與使用指南-大金空調除濕標志:了解含義,掌握使用技巧 智能變電站巡檢:機器人的角色與未來-變電站巡檢機器人的技術創新與應用發展
智能變電站巡檢:機器人的角色與未來-變電站巡檢機器人的技術創新與應用發展 高鐵上大學生幫了11歲時的自己-5月6日上午熱點新聞
高鐵上大學生幫了11歲時的自己-5月6日上午熱點新聞 網購迪士尼套餐最終民警護送入園-網購迪士尼套餐最終民警護送入園,女子稱遭網店欺詐威脅
網購迪士尼套餐最終民警護送入園-網購迪士尼套餐最終民警護送入園,女子稱遭網店欺詐威脅 原來上班真的能跨越階級-上班就能跨越階級!從一無所有到一毛不拔~
原來上班真的能跨越階級-上班就能跨越階級!從一無所有到一毛不拔~ 《八項注意三大紀律》的深刻內涵與當代價值-解讀《八項注意三大紀律》的歷史背景與現實意義
《八項注意三大紀律》的深刻內涵與當代價值-解讀《八項注意三大紀律》的歷史背景與現實意義 OPPO在線客服:一站式服務解決方案-了解OPPO在線客服的重要性及其優質服務
OPPO在線客服:一站式服務解決方案-了解OPPO在線客服的重要性及其優質服務 美聯儲連續第六次維持基準利率不變,鮑威爾稱下一步行動不太可能是加息,哪些信息值得關注?
美聯儲連續第六次維持基準利率不變,鮑威爾稱下一步行動不太可能是加息,哪些信息值得關注?